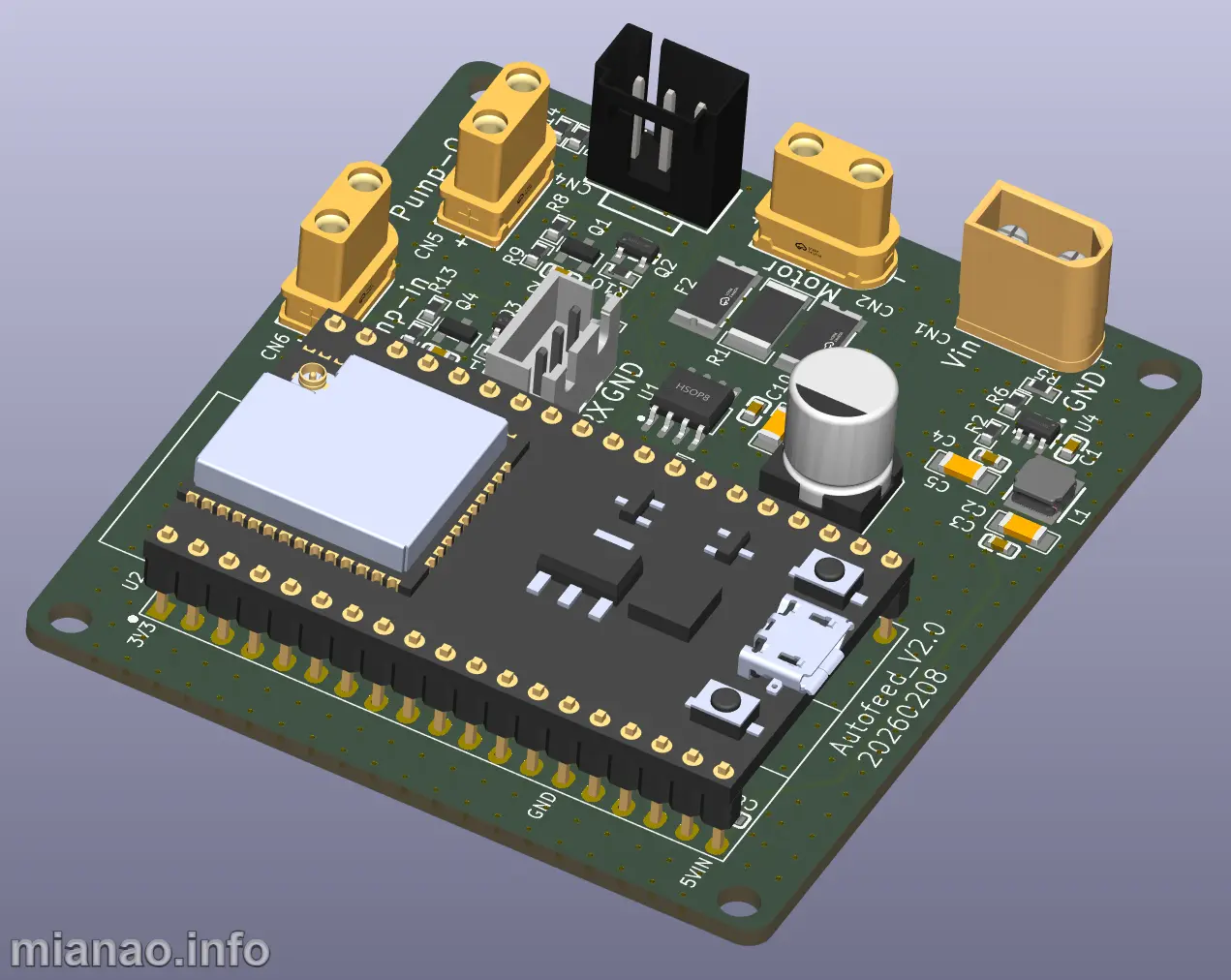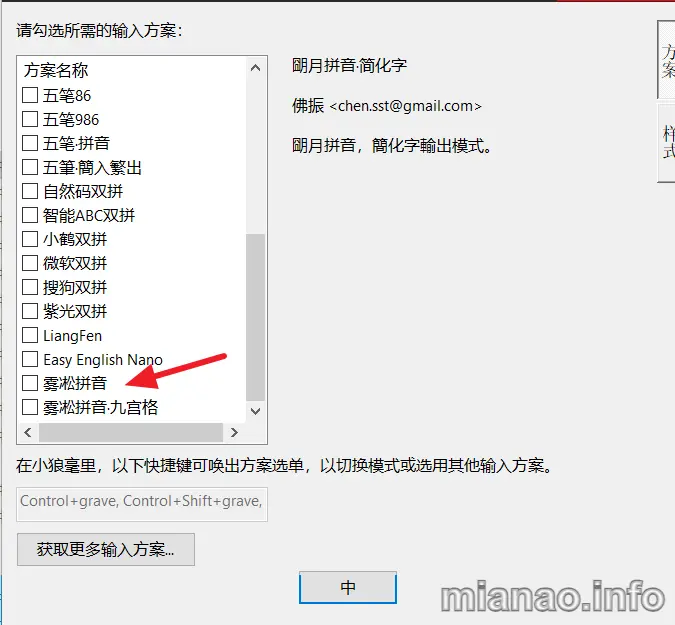转载:所多码-梁文道
歡迎來到所多瑪。且讓我為你介紹這座城市裏所剩不多的善人。
例如許志永,香港中學生鄭詠欣最近才在報刊上為他發表公開信,呼籲溫家寶“用法理來說服我”,有情有理,令人慨歎,是一時焦點。在我看來,這封信最令人神傷的,是鄭小姐記述許志永被捕幾個月前還親口對她解釋別看截訪的公安很野蠻,而要注意事情好轉的那一面,他說:“中國政府已很努力,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
你知道,每次在香港和臺灣向別人介紹今天大陸的情況,都有人批評我的立場太過曖昧,取態太過溫和。他們認為中國政府仍然是大海中那頭兇猛的巨獸,獨裁專制,噬人無算,而且絕無任何溫和漸變的希望。而每一次,我都會告訴他們真實的情況很複雜,不要簡單地總體化中國的問題,不要用刻版的偏見來看中國,而且要對政府有點耐性。
我的朋友許知遠也寫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我們這一代》,他說許志永兩年前曾經意氣風發地對他表示“2008年的奧運會將給中國帶來一次巨大變革機會。當全世界都盯著北京時,政治權力將有所收斂,而不同民間組織都時刻利用良機,拓展公民社會的空間”。這番話我一點也不陌生,因為我也表達過類似的意見,我也曾對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之後的中國充滿信心。每當外國記者找我談論中國的黑暗角落,我都會在最後提醒他們,永遠要看到光明的那一面,就如我曾提醒你一樣。
而那光明的一面,就包括許志永和他公盟裏的同伴,以及正在崛起的維權律師群體,與其他無數想做好事的熱心人。這個國家腐敗,這個社會冷漠,整個局面似乎就維繫在一個十三億人關於某則謊言的默契之上。儘管如此,卻竟然還有這麼多人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去替陌生人的子女奔走,如譚作人;竟還有這麼多人願意犧牲自己本來可以享受的生活,去替苦難無告的同胞叩門,如許志永。我甚至樂觀到把政府也算進這光明的一面,因為至少他們曾經容許這種昏沉裏的光芒搖曳。也許他們明白,連他們自己人都紛紛卷款而去,用腳對這裏投下不信任票的時候,好人的存在有多麼重要。天不喪予,如果你還能在所多瑪找到一個好人的話。
他們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外面,自由自在地上學成長,卻讓我們的孩子背負債務來接受可笑的教育;他們將自己的家人搬到北美和歐洲,享受乾淨的流水和清新的空氣,卻留給我們一片受傷並且中毒的土地。這個國家腐敗如此,這個社會已然冷漠若斯。現在他們居然還要扼殺好人,並且恐嚇其他人打消當好人的念頭?沒錯。所以當你在公車上被人打劫,高聲求救,卻發現滿車沒有一個人會伸出援手,甚至還別過頭去的時候,不要訝異,因為我們鼓勵這樣的風氣。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當好人也不是不行,但前提是儘量不要自發。等到他們動員你了,你再調動自己的善念不遲,就像一個演員調動情緒來刺激淚腺一樣。在這裏,好人最好都是配合政府登場的演員,善意是種需要學習的演技,善惡的標準不來自頭頂的星空,也不來自內心永恆的道德律,而在感動中國所界定的範圍。你千萬要小心,知道有人淩辱女子,可不能隨便告發,因為你不知道那個強姦犯是誰,但如果聽說一場運動會要召募志願者了,那你得踴躍報名,不落人後。
忘記許志永吧,忘記那些你心目的好人,不要用你高高在上的標準來看待我們,對我們指手劃腳。因為我們中國有自己的模式和道德尺度。
對了,聽說過北京南站附近的“聚源賓館”嗎?裏頭監禁了許多被攔截下來的上訪者,就是許志永會幫助的那種人。他們居住的條件很惡劣,看守他們的人也很兇暴,偶爾還會強姦其中弱女。但許志永明明知道這種情況,卻還要對香港來的女學生說“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這只是因為他太善良了。
如今,好人譚作人和許志永終於消失了,剩下那批上訪者還在聚源賓館裏面呼救呻吟。半夜,他們唱歌,希望引起外頭的路人注意。據說他們唱的是《國際歌》,而中南海就在五公里之外,據說他們唱的是《東方紅》,而毛澤東紀念堂就在五公里之內。歌聲由激憤漸轉悽楚,終於泣不成聲,而街燈,兀自孤冷地亮著。
我不知道你回去之後會如何報告,你明白,中國人是不信邪的。我也早就背棄了你和你所代表的一切。如今,我將留在這裏等待利維坦卷起的巨浪迎岸而來。
我另一個朋友,臺灣評論家楊照,曾經在《十年後的臺灣》裏寫下這麼一段我屢次引述的話:“我還記得,我清楚記得,自己年少時候,被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震駭,領受到那股歷史性的悲劇感。國民黨威權體制像只怪獸,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運動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這只怪獸想:不會再有人敢違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將站在怪獸面前,即使明知將成為下一個犧牲者,即使內心害怕得渾身發抖,也還是得挺身站在那裏。因為,讓怪獸吞噬,是惟一能夠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夠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夠證明我們自主意志尚存的動作,不能放棄”。
他接著說:“我從來不曾自認是個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卻悲劇性地預見:等時機到了,我這一輩的人,會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與猶豫,去站在怪獸面前,被無所不在的極權系統監視、追捕、入獄”。
我知道自己不是善人,但我寄望自己能夠通過那未來的試煉,證明自己。所多瑪,一座惡貫滿盈的城市,它的善人皆以其自身的消亡來證明這裏仍有善人。
奖励链接: 欢迎使用推荐链接,新用户充值有奖励 https://www.vultr.com/?ref=7342510